
我手中的这枚古钱币来自中国大西北那条著名的走廊——河西走廊。具体一些说,它来自甘肃的武威。
铜钱也许司空见惯,但是这一枚非同凡响——它是古代中国第一种以国号为钱文的圆形方孔钱。
2017年,中国的丁酉年,我到武威参加朋友的一个新书活动。当然,不言而喻,此类活动总是有着旅行的意味。活动之余,游荡在武威的街头,一座筑成钱币模样的雕塑吸引了我。与其说“吸引”,倒不如说是略感惊诧。尽管物质主义已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甚嚣尘上,但悍然为“方孔兄”筑碑,还是会有些令人瞠目。
武威是什么地方?此地古称凉州,雍州,姑臧,休屠,屠各,是古西北首府,六朝古都,是为天下要冲,国家蕃卫。它以汉武帝为彰显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大凉在此建都。这里曾经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这一定会令你吃惊,至少,若不是旅行至此,我自己是难以想象这个史实的——武威在古代中国的某个时期,有着今天“北上广”的地位。
如今提及河西走廊我们会想到什么?不错,是边塞,是不度玉门关的春风,是西出而去便无故人的阳关。这一切的“经验”或者“常识”,也许皆是拜文学所赐。伟大的唐诗塑造了我们对于河西走廊的空间想象,但是,显而易见,文学的事实在许多时刻只服从文学家主观的心情。一千两百多年前,唐玄宗开元25年,当诗人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旨的时候,他看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既是诗人王维那一趟旅途的自然风貌,更是诗人王维那一趟旅行的个体心情。
实际上,王维此行,去往的是中国第三大城市的方向。如同今天,我由西北而东南,走向了上海。
2017年,中国的丁酉年,我在武威的街头叹息时空的更迭,叹息文学是如何打破了历史的真实与想象的界限。春风薄凉,夕阳昏黄。一座筑成钱币模样的雕塑吸引了我。它的底座上镌刻着“凉造新泉”这四个字。
是四个字的音韵在一瞬间打动了我,加之薄凉的春风,加之昏黄的夕阳,当这一切在一次旅行中集体作用在一个小说家的身心之时,那个写作的“动机”得以形成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是的,这四个字的音韵在一瞬间令我做出决定——我要为此写下一个短篇小说。
听起来这也许有些玄奥——四个字的音韵便足以策动一个短篇小说的书写,足以成为一个写作的“动机”。其实连我自己也是难以说得清楚。毋宁便将玄奥的发生推诿于旅行的展开。
写《威克菲尔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驱使?是什么召唤了塞林格,让他写出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之所以不去以《红字》猜度霍桑,是因为相较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似乎更容易被描述,它们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身躯,并且,描述起来也容易满足人类追求“确凿”的本能,换一种说法,就是它们也许更容易被说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感,它们难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难以被轻易地表达。就好比,当我们力图去说明“灰色”时,总是会比力图说明“红黄蓝”时感到吃力和为难。那么,为什么不以《九故事》来整体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为,当九个短篇被他集体命名后,“意图”扩张,于是“意义”彰显。而这构成“整体”的“九分之一”,显然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它独立成章的时候,必定没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规划性”。打个比喻,一本小说集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一栋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个篇章,或许只是局部中的残垣断壁。
干脆下个结论吧:在我看来,旅行与短篇小说天然有着可以通约的本质,它们能够被我用来相互映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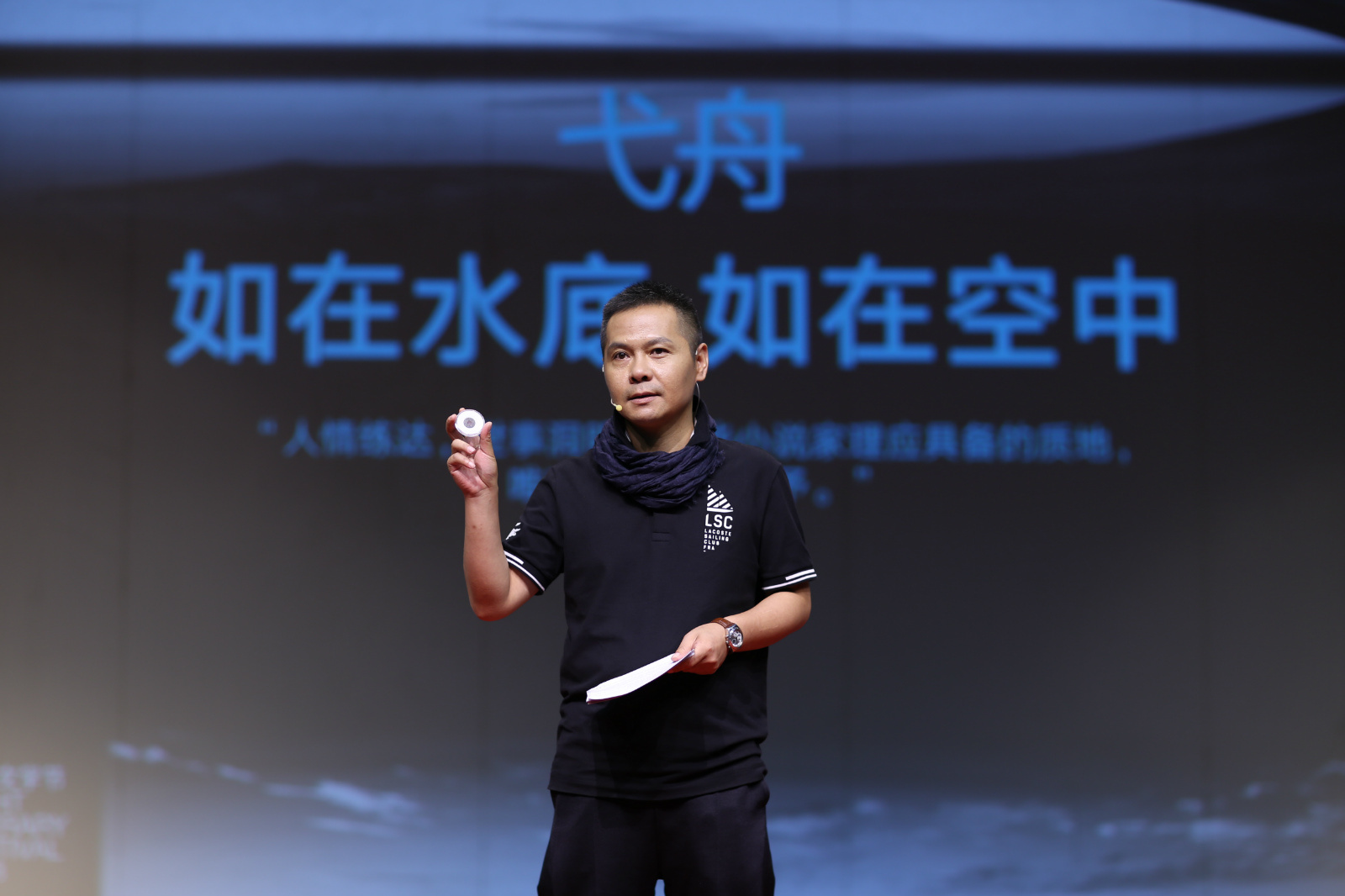
在旅行中,真实与虚构的共振才能最轻易的发生,因为此刻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体味把握的同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流逝感也一并发生。是旅行令我们有了玄奥的能力,令我们敏感而脆弱,令我们在一种迥异于日常状态的整体性的叙事中,以看得见的风景决定出了自己内心看不见的风景。
“凉造新泉”,“凉”是西晋十六国时期在河西一带建立的国号名,“造”是“制造”,“新”是“新旧”,而“泉”,在古代汉语中通“钱”。不是吗?这很好理解。
蒲唯定睛端详古币上那颗唯一被自己触摸出名堂的字——原来它的笔画最简单,当你一旦确认出它,它就像脑筋急转弯后那个浅显的谜底,令你有种轻微的羞耻之感。蒲唯想,这其实没什么了不起,“钱”通“泉”,这对于一个学过古汉语的人而言,几近常识。与其说他是摸出了这个字,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的经验给了他指尖以灵感。
不错,这已经是小说中的段落。
在小说中,我让这枚“凉造新泉”掉入了水底。
现实中,这枚钱币价值不菲,它的上品拍卖价格将近三万元人民币。现实中,如果我的三万块人民币掉入湖中,我想,以我贪财的本性,十有八九,我会下水去打捞的。在小说中,男人们也这么做了,但他们前赴后继,为的不是三万块人民币,为的是一种莫须有的盼望和宝贵的憧憬与相信。
脚下踩到湖岸时,出水的蒲唯发现自己泡皱的双手除了挂着水草,右手食指上还缠着根五彩绳,绳子上系着的,可不就是那枚“凉造新泉”。对此他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好像他深入到水底去,就是为了把什么丢失了的再找回来似的;好像只要他伸出手去,必定就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将重新被攥在手心一样。
于是在小说中:
他一步一步从水里蹚出来,浑身的划痕,唯一能做的就是忍住不发抖。他的腿在抽筋,肌肉一阵阵跳动着痉挛。不管昨晚程小玮经历了什么,他可不愿意被人拖上岸。他对自己说,好吧,我来过了,沉下去了,伸出手了,现在,我“必须”走出来了。
当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对自己说:好吧,我来过了,沉下去了,伸出手了,现在,我“必须”走出来了时,我想,他就是在诉说一种旅行的心情。
这种心情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在所有难辨真假的叙事中,以文学的方式,带我们到达未知的远方,让我们探究自我存在的意义。
此刻我手中的这枚“凉造新泉”并没有掉到湖底过。但谁知道呢,毕竟它有着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看到过旅行者王维从身边走过,看到过旅行者王之涣从身边走过。这枚“凉造新泉”是我为了此次上海之行特意向友人讨来的,我说“借”,他说“送”。送给我我是断然不敢领受的,不是我觉得三万块人民币过于沉甸甸,是我更向往领受这沉甸甸的情谊。而此番情谊,也要拜那一趟旅行所赐。那一趟旅行,让我收获了远方的风景,收获了一个短篇小说,还收获了无可估量的友谊。
重新将目光投向湖面,蒲唯的心情又一次跃入了水中。水面扩散着亿万道细碎的波纹,像是释放着大自然亘古以来难以穷尽的隐秘的痛苦。尽管蒲唯知道那道光不会重现,但心里还是如同水面一般涟漪涌动。没错,蒲唯想,他真的可能有幸目睹过一道圣光,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有那么一会儿,蒲唯变成了他不自知的观察者,他看到这些天里,两个生活中的受挫者怀着羞于启齿的等待之情,在“写信的人如今就在写信的地方”那样一种宽泛而朴素的理解力下,试着靠近过那道光,从而和一些有希望的东西再次发生了联系。为此,他们前仆后继,不惜涉险——即便那莫须有的事物宛若捕风捉影,即便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是的,这个短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它孕育于一次旅行,也描述了一次旅行,在我看来,这个短篇小说的名字,也堪可被视为我对于旅行的全部体认。最后,它当然收录在了我最新的短篇小说集《丁酉故事集》中。
该专辑其他节目
- Part1 下午开场
- Part1 米亚科托|每个词都是一场旅行(译文)
- Part1 米亚科托|每个词都是一场旅行(原声)
- Part1 恩格伦|蛀洞:时间旅行的极简历史(原声)
- Part1 恩格伦|蛀洞:时间旅行的极简历史(译文)
- Part 1 李敬泽|消失的旅行者
- Part1 苏阳|黄河今流:从同心路到麦德林
- Part1 恩里克|辣椒与漆器:中国,墨西哥,第一次全球化(原声)
- Part1 恩里克|辣椒与漆器:中国,墨西哥,第一次全球化(译文)
- Part2 马家辉|旅途上的离散与重遇
- Part2 万之|我的西行记:在异乡“寻源”
- Part2 翟永明|两个弗里达
- Part2 小白|文字历险:历史迷雾里的人
- Part3 晚上开场
- Part3 李陀|思想的旅行
- Part3 文珍|旅行就是越过自我的边界
- Part3 弋舟|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 Part3 王咸|日常生活就是我的旅行
- Part3 林婉瑜|诗和流行音乐,爱情与远行
- Part4 詹宏志|远方的鼓声:古城的召唤
- Part4 李宏伟|三本书标识的旅程
- Part4 田耳|与旅行无缘的旅者
- Part4 袁凌|《世界》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