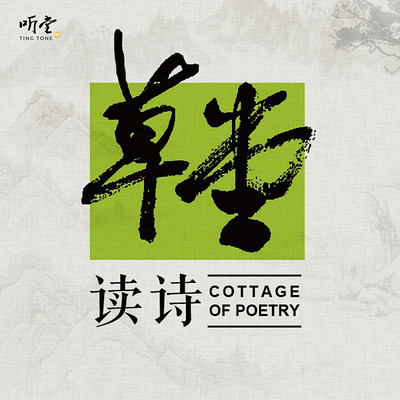诗人:康承佳

武汉大学研究生在读,90后重庆山城姑娘,爱文字,爱土地,无宗教信仰,但热爱诸神和上帝。作品散见于《诗刊》《草堂》《星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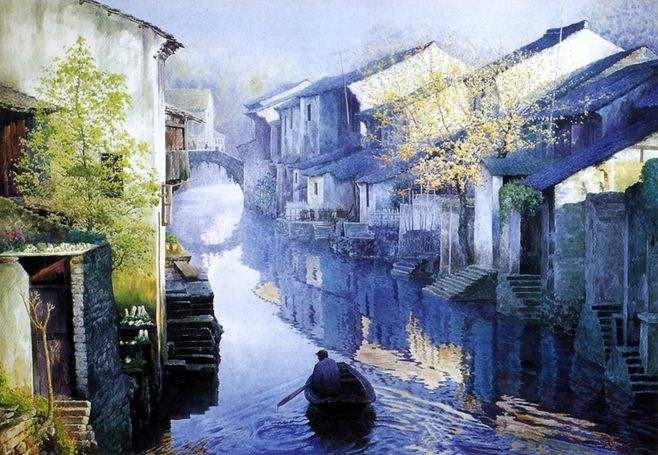
《先生,这一生》
先生,这一生,故土极远
常有母亲的病痛祖父的死,以及
从儿时开始就到不了的远山
该有多绝望,大地上
村庄坐失于土地和拆迁
先生,这一生,春天有绿
从桉树的伤口到小麦的鹅黄,还有
枝头一闪而逝蝴蝶的翅膀
该有多安慰,人间词话
只是我们默契而相似的孤独
故事: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发展必然带来阵痛,乡土文明也在逐渐失落,康承佳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所以她的很多作品,灵感都是来源于此。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先生,这一生》这首诗,也是如此。
康承佳出生在西南山城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四面环山,一条换季就断流的小溪从村头贯穿至村尾,也贯穿了她孩提时代最灵动的记忆。她的童年干净、寂寥、一尘不染。康承佳自小就和土地亲,山川上的炊烟,山川上的坟墓,山川上的四季轮回,她都如数家珍。
康承佳努力地感受故乡的万事万物,她觉得对于幼小的她来说,最初的启蒙,就来自于一个幼稚孩子对于自然山川最原始最澄澈的好奇。而对“万物有灵”的领受是古老的村子对一个初生的孩子最大的赋予与馈赠。
康承佳第一次感觉到生活和土地的剥离,是六岁入学的时候,但那个时候,是没有惆怅的,甚至因为新鲜,多了好些惊喜。她念书的地方是和村子隔了好几座山的小镇,小镇对于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富饶,热闹,人群拥挤。
她喜欢小镇有甚于村子,毕竟,穿过几条老街就能抵达学校,学校,对于一个自出生就封闭在山沟沟里的孩子来说,太过于神奇甚而神圣。每天都会天不亮就起床,翻山越岭特有仪式感地去镇上上课,咿咿呀呀地跟着老师念:“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其实,就算老师深入浅出地解析了里面潜藏的城乡二元对立发展背后农村底层手工业者的心酸,但她依旧对于那样遥远模糊的情绪无感,因为在她那时候的认知体系中,这仍然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诗意书写,能够作为农民的孩子内心是说不完道不尽的饱满和丰盈。
那个时候,土地,对于自小就在泥浆子里打滚长大的孩子是特别有亲切感的,衣食住行的种种,都是土地的赋予。那时候即使祖父年迈,身体也还算硬朗,每天放学回家,康承佳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大黄狗一前一后屁颠儿屁颠儿跑去陪祖父除草,她乐此不疲地蹲在田坎上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邮件,就连座机电话都是好几年之后的事儿,人和人联系就是出门登高,扯着嗓门儿一吆喝,对面就能听到,于是对方也爬上山头来对聊,聊天内容悠悠地荡在山坳里,弥久不散,荡到了多年以后,依旧浓得化不开。这就成了她乡愁的起点。
高考之后,康承佳离乡,她知道,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离开,注定是终生性的。而之后,她的父母也将离开那片土地。母亲打电话告诉她,家乡退耕还林,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出台政策,整个山区集体搬迁。于是,康承佳准备回家乡一趟,总有些告别,是以“不再见”为前提的,所以她想让最后的 “再见”郑重一些。
坐火车回家,随行带了《乡关何处》,野夫先生说:“不管怎样变迁荒芜,我以为,有故乡的人仍然是幸运的。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他们许多都不知所云。他们的父母一代是有的,但到了这一代,很多人都把故乡弄丢了。
城市化和移民,剪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康承佳觉得,文字是有痛感的,尤其是对于她这样的遗忘故乡同时也被故乡遗忘的异乡人,字字句句都砸在了心上。
回到家乡,眼前的农村,安宁,平静,一切都很慢,但同时,贫瘠,荒凉,滞后于整个时代。城市的生态却截然相反,小步快跑急速迭代,康承佳知道,自她开始下一代对于土地的认知可能几乎无感,但面对必然,何去何从只能都交给时间。只是她觉得,此去经年,她的乡愁已无可附着,为什么会思乡,毕竟,就精神层面来说,她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该专辑其他节目
- 赏析:胡弦《咖啡馆》
- 朗诵:杜涯《为一对老夫妇而作》
- 故事:马克思《思念》
- 赏析:余笑忠《梦醒后》
- 声音里,诗歌写就的成都
- 2019猪年大吉 听堂FM全体主播给你拜年了!
- 故事:老井《化蝶》
- 赏析:博尔赫斯《分离》
- 朗诵:马拉美《撞钟人》《天鹅》
- 故事:宋晓杰《节日的酒局》
- 赏析:宗小白《春日篇》
- 朗诵:W·S·默温《致新年》《愿望》
- 朗诵:梁平 《想兰州》
- 故事:戴望舒 《雨巷》
- 赏析:费尔南多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 故事: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
- 赏析:纪弦《火葬》
- 朗诵:奥登《爱得更多》《小说家》
- 故事:张枣《镜中》
- 赏析:何其芳《预言》
- 朗诵:梅特林克《老的歌谣》《假如有一天他回来了》
- 故事:康承佳《先生,这一生》
- 赏析 : 穆旦《冬》
- 朗读:惠特曼《我在路易斯安那看见一颗栎树在生长》《从滚滚的人海中》
- 故事:罗门《诗的岁月—给蓉子》
- 赏析:冯至《十四行诗》
- 朗诵:杨键《冬日》《夫妇》
- 故事:蓝蓝《矿工》
- 赏析:郑愁予《小小的岛》
- 朗诵:昌耀《良宵》